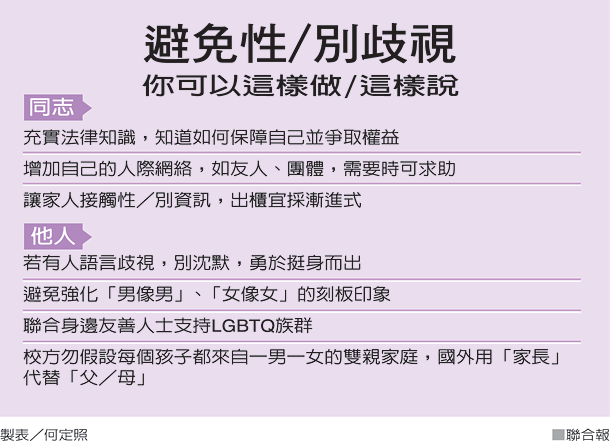當沉默比訴說更加痛苦時,人們便開始書寫。我將一直以來被死死壓抑的那些關於我身體的故事化為文字。
在陳述了墮胎經驗後,我也將約會暴力、約會強暴、第一次性行為、第一次自慰、第一次高潮、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工作、非獨占的多邊戀、不婚、不生等,因太過私密而被捨棄的故事寫了又寫。身為女性的我,如此談論性愛、墮胎手術,甚至是性工作經驗等話題,等同踩過紅線踏入禁區。
無論是誰、無論是什麼樣的存在,都無法將我困在那紅線框架之中。赤裸的我雖一絲不掛,卻無一絲羞恥。「紅線上的非體」,偏離既存秩序的骯髒軀體。因骯髒而獨特且無法被界定的存在。
女孩對性的羞恥感 方便了誰?
十五歲時,我交了一個大我兩歲的男友。我們常常趁他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去他家吃零食、看電視,或者訴訴苦、開開玩笑,一下子天就黑了。有一天,他說:「白色情人節那天要做什麼呢?來偷喝點啤酒吧!」
那天我像平常一樣去到他家,而他跟他的朋友正聚在一起。他們看起來已經喝了不少,一邊祝福著我和男友,一邊替我倒酒。
雖然也想過跟一群陌生男人在一起會不會有危險,但沒過多久我就沉浸在氛圍之中,飲下啤酒。身體漸漸無力開始頭暈。這可是白色情人節啊!我不想搞砸這麼重要的紀念日,但最終還是決定自己待在他的房間休息。
不知道我睡了多久。他進到房間輕輕撫拍我的背。他躺到我身邊,相望的我們開始撫摸對方的身體。他的手慢慢往下探索,伸進我的內褲裡。「這是什麼意思?現在這是什麼狀況?」我想起國小看過的性教育影片《我的身體是寶物》。我應該對他說:「不要!」、「我還沒準備好。我不想要這樣的第一次。我現在狀態不太好。」雖然在心裡不斷重複,但我卻說不出口。
「可以嗎?」他開口問。我無法說不。如果他因為我拒絕而討厭我該怎麼辦?是不是不該破壞氣氛?我還是不想要;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喝了酒,身體不聽使喚。耳邊傳來他的朋友在客廳嬉鬧的聲音。不是強迫卻也沒經過我的同意,在我朦朦朧朧的狀態之下,他那不屬於我的部分,他的性器進入了我的身體。
就讀女中的我很喜歡跟朋友閒聊女孩的桃色八卦。「聽說她跟男朋友睡了」、「聽說有個高中的姐姐因為懷孕申請退學」、「聽說她是個破麻」、「真髒」。我做了她們口中的骯髒事。有天,某個朋友把我叫出去問我:「你是不是跟某某某睡了?」朋友盯著我看,好似叫我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。
但我仍舊與那時的男友維持著戀人關係,喝醉的時候偶爾也會去找他。我們在那之後也發生過幾次關係。我想要修正被摧毀的第一次,也想確認他不只是「玩玩而已」。
他們視女人為待價而沽的性感商品
若說我的性在青少年時期與叢林般的力量相連結的話,成年後就是和社會經濟權力相連。
那時我十九歲,在一家日本料理店打工。與時薪不到三千韓元的速食店不同,那裡的時薪是七千元。工作內容是穿著若隱若現的浴衣端菜,坐在客人旁邊把刺身套餐的生魚片夾進他們手邊的盤子。雖然必須忍受性騷擾言論以及油膩的目光,可是客人的小費給得很大方。
二十五歲左右,一起從事藝術活動的前輩對我說:「女人只要下定決心,成功只是小菜一碟。因為在性方面有商業價值,所以容易受關注。」他們全都羨慕身為女性的我。
但他們羨慕的「女性」,侷限在沒有身心問題、不胖也不老的女性。「年輕貌美的女人」這個符合大眾口味的食品,在世上十分常見。即使在性方面沒了商業價值,即使遇不到有錢配偶,我也不想成為隨時會被取代的食品。
看穿性暴力背後的權力不對等
當時我正和某文化企劃團代表在他的辦公室裡談話,邊喝啤酒邊分享我做過的事情及長久以來的煩惱。我那時非常需要文化企劃領域前輩的建議和幫助,他也很清楚這件事。
就在談話差不多結束時,他吹熄了原本放在我們兩人中間的蠟燭,靠近我問道:「我可以吻你嗎?」接吻也沒什麼,但那雙企圖剝去我衣服的手讓我很不舒服。我並沒有要和他上床的想法,更何況是在他那間隨時都可能有人進來的辦公室裡。當我抓住他的手準備拒絕時,他問我:「你討厭我嗎?」我並不討厭他,只不過覺得這個狀況讓我不舒服而已。「不,不是這樣……」,我含糊地回應他。
如果現在冷漠地拒絕他,我們的關係會不會變得很僵,這個想法從我的腦海掠過。若是這樣,以後就很難再找他幫忙,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。
他上下其手愛撫我的身體後,將性器插入。
我之後才知道,他也用一樣的方式(蠟燭、啤酒、悠揚的音樂、辦公室、工作)接近我姊姊。而他過去也曾利用類似的方法向其他女人求歡,甚至曾經因為爆出性醜聞而短暫停止活動。
他自始至終都自在從容。權力打從一開始就不會強行侵犯你;並沒有這個必要。
正因為他們手握權力,所以不需要強迫,只需繼續扮演謙謙君子。